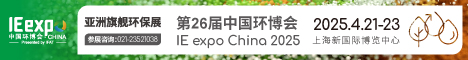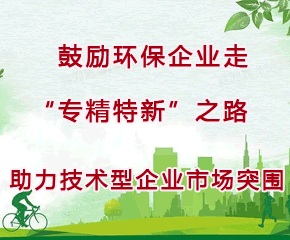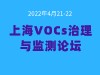非現場監管方式大量應用,如何規范?
更新時間:2025-10-13 10:37
來源:法治日報
作者: 陳海萍
閱讀:2221
【谷騰環保網訊】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提出“探索推行以遠程監管、移動監管、預警防控為特征的非現場監管,解決人少事多的難題”。近年來,實務部門秉承解決龐雜監管任務與稀缺監管資源沖突之理念,已陸續采用自動識別、預警提示、自動整改和消除違法后果相結合的遞進式非接觸式監管方式。非現場監管是以干預方式限制相對人自由或財產權的一種執法手段。雖然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術加持下提升執法效能、有效節約執法成本,但同時潛藏了法律依據不足、算法不透明、有可能使當事人程序權利受損和簡單機械執法等風險。因此,如何看待非現場監管方式對傳統執法帶來的沖擊,非現場監管方式為何以及如何在法治范疇內依法進行,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勢在必行。
相對傳統的“人—人”交互式特點,“人—系統”對話式的非現場監管特別有利于瞬間性違法行為的固定和批量行政的處理。該執法方式既能屏蔽人為干預的主觀考量,又能確保監管決策的正確性。就此而言,非現場監管方式回應了減輕相對人負擔、提高監管效能、優化營商環境等監管要求和政策目標。
針對非現場監管方式的應用優勢,學界基于對技術權力不可控且沖擊相對人合法權益保護的擔憂,呈現了從警惕至開放的不同認知維度。從采集監管數據、固定事實的輔助行政,到通過在線監管系統發布自動行政,再到允許有裁量空間的完全自動行政等,都有支持者。由此可見,理解非現場監管方式的創新性應用,實質上是對技術可以代替執法人員這一前提持肯定立場,但可否全程代替事實認定與適用法律這一行政能動作用,則需從應用范圍和程度建構其制度可能性。
非現場監管方式應用范圍的確定,需依循“認事用法”行政執法規律。以“認事”展開的非現場監管,可根據被監管者的物體性質和相對人行為特性,分別確定應用范圍。對諸如涉及設備的數據監管,有條件應用則應用;對相對人的行為監管,則又需依相對人行為危險性進行分級應用。而內含執法人員找法、解釋、涵攝等一系列“用法”活動,原則上不應納入應用范圍,除非法律允許且滿足下列要件。例如,不逾越人格畫像、個人信息保護與平等為其主要基本權利的界限,符合行政保護安全、自動系統充分測試以及排除法規范連結因果關聯等,此時容許有應用可能性。
對于非現場監管方式應用程度,可運用行政執法“自動化深度”和“法律監管強度”兩個基本變量予以界定,構建強度有別的梯度化應用類型。對依托電子設備易于判斷、適合高度自動化領域,若無裁量且監管強度低,則最適合深度應用;若有裁量且監管強度亦高,則原則上盡量應用。而對依托電子設備難于判斷、適合淺度自動化領域,若無裁量且監管強度低,則原則上輔助應用;若有裁量且監管強度亦高,則盡量不應用。
傳統監管過程中,執法人員依法告知和說明理由的威嚴執法形象,與相對人申辯、配合和容忍的主體人格形象,組合成一幅幅“人—人”交互理性圖。而由自動化系統載體和算法權力構筑的非現場監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這種理性。第一,教育公眾守法、預防再次違法的監管目的被消解。第二,被監管者隨時以潛在違法者的地位被處理。第三,政府和公民間信任關系的構建無以立足。
在“機器無法進行價值判斷”理念的貫徹下,非現場監管的法治風險爭議一直圍繞下列問題持續進行著:一是法律適用邊界不明確。人工智能與信息技術的賦能,使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愈發復雜。二是在線監管系統彈性措施設置不足。法律適用程式化的非現場監管方式,天然攜帶忽視個案特殊情節的基因缺陷。三是算法權力與算法規則不透明。被監管者據以對抗的法定權利被拋棄,因果利害關聯主張無法實現,行政法律責任歸屬模糊。
上述非現場監管方式的法治風險,集中在相對人程序權利被壓縮和減省的前提之下。完善以正當程序原則為重心的非現場監管規范體系,是目前最適當的可取之道。
在為非現場監管設定界限過程中,讓公民參與立法過程,盡最大可能實現“法律適用邊界明確”的民主控制功能。在具體執法領域,賦予相對人異議權以防御程式化監管沖擊個案正義,充實“在線監管系統彈性措施設置恰當”,確立非現場及時轉化為現場的銜接機制。執法機關應及時公布算法規則,確保“算法透明”和可理解性,回應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的行使需求;同時配備專業技術官員,有效解釋算法規則,從而確保相對人陳述申辯權的充分行使。最后,對上述執法機關保障方式與保障程度是否合法妥當的爭議,賦予利害關系人向有權機關請求救濟的權利,從而在技術效率與法治原則間尋求平衡,最終實現保障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法治使命。
(作者系上海政法學院法律學院教授,憲法與行政法教研室主任)
聲明:轉載此文是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作者持權屬證明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使用微信“掃一掃”功能添加“谷騰環保網”